福德文選:謝天
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。當蠟燭燃起,菜餚布好,客主就位,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,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,並歡迎客人的到來。
我剛一到美時,常鬧得尷尬。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,還沒有坐好,就開動了。
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,總是先囑咐自己,今天不要忘了,可別太快開動啊!幾年來,我已變得很習慣了。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,在我這方面看來,忘或不忘,也沒有太大的關係。
前年有一次,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。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。她雪白的頭髮,顫抖的聲音,在搖曳的燭光下,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。那天晚上,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。
在小時候,每當冬夜,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。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,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;「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,記住,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,要是糟蹋糧食,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。」
剛上小學的我,正念打倒偶像,破除迷信,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,我的書桌就是供桌。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,給關平戴上鬍子,祖母的話,老天爺也者,我覺得是既多餘,又落伍的。
不過,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,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,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。
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,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。
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。多少年,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。
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,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,我想起我的兒時;由於我的兒時,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。
祖父每年在「風裏雨裏的咬牙」,祖母每年在「茶裏飯裏的自苦」,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,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,而為什麼要謝天?我明明是個小孩子,混吃混玩,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?
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,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。
一直到前年,我在普林斯頓,瀏覽愛因斯坦的《我所看見的世界》,得到了新的領悟。
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,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、在歡迎會上啦、在朋友的葬禮中,他所發表的談話。
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: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,就是由於乙,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。
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,並無參考可引,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,「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。」
其他的文章,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,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;這種謙抑,這種不居功,科學史中是少見的。
我就想,如此大功而竟不居,為什麼?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,像我祖母之於我家。
幾年來自己的奔波,作了一些研究,寫了幾篇學術文章,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,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:即是無論什麼事,得之於人者太多,出之於己者太少。
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,就感謝天罷。無論什麼事,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,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,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。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,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。
於是,創業的人,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,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。
介之推不言祿,祿亦弗及。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。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,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,是君子所不屑為,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。
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,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,他說五千。主任說:「給你五千,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?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!」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?
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?立過大功,而不居功若此。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,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,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。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、感謝上天的感覺。
我們回頭想一想,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!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,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,無法與無天的時代。
無論哪一行、哪一界,多是自吹自擂,自欺自騙。日子長了,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,而大禍至矣。
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,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,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。
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,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。
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,我記得是雨果罷,「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,而只許留一本,應留什麼?」雨果毫不猶豫的說:「只留〈約伯記〉。」約伯是《聖經》裏面的介之推,富亦謝天,貧亦謝天,病亦謝天,苦亦謝天。
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,需要約伯的精神,需要介之推的覺悟。這個覺悟即是:一粥一飯,半絲半縷,都是多少年、多少人的血汗結晶。感謝之情,無由表達,還是謝天罷。
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
本文摘錄自《在春風裏》
文章來源:陳之藩文集
圖片來源:柔光照耀的房間裡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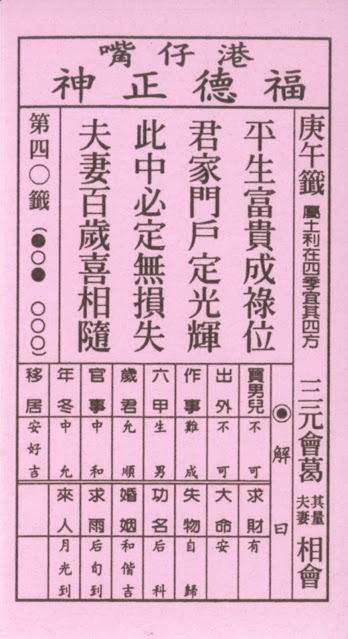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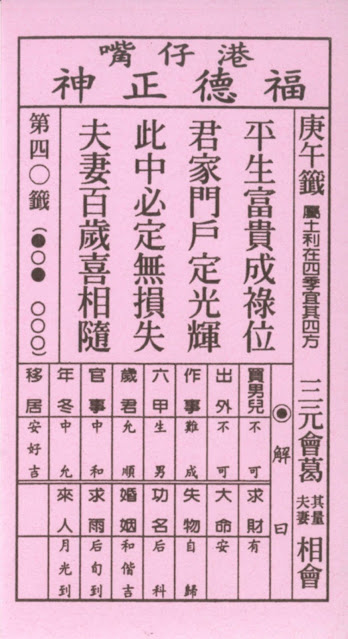
留言
張貼留言